新闻动态
- 发布日期:2025-11-19 06:18 点击次数:18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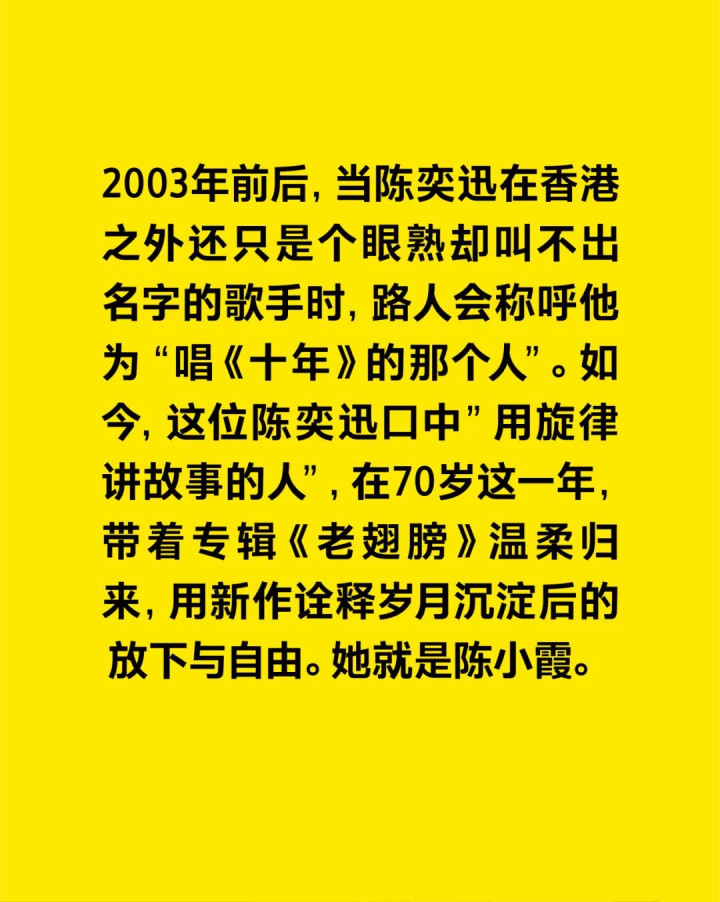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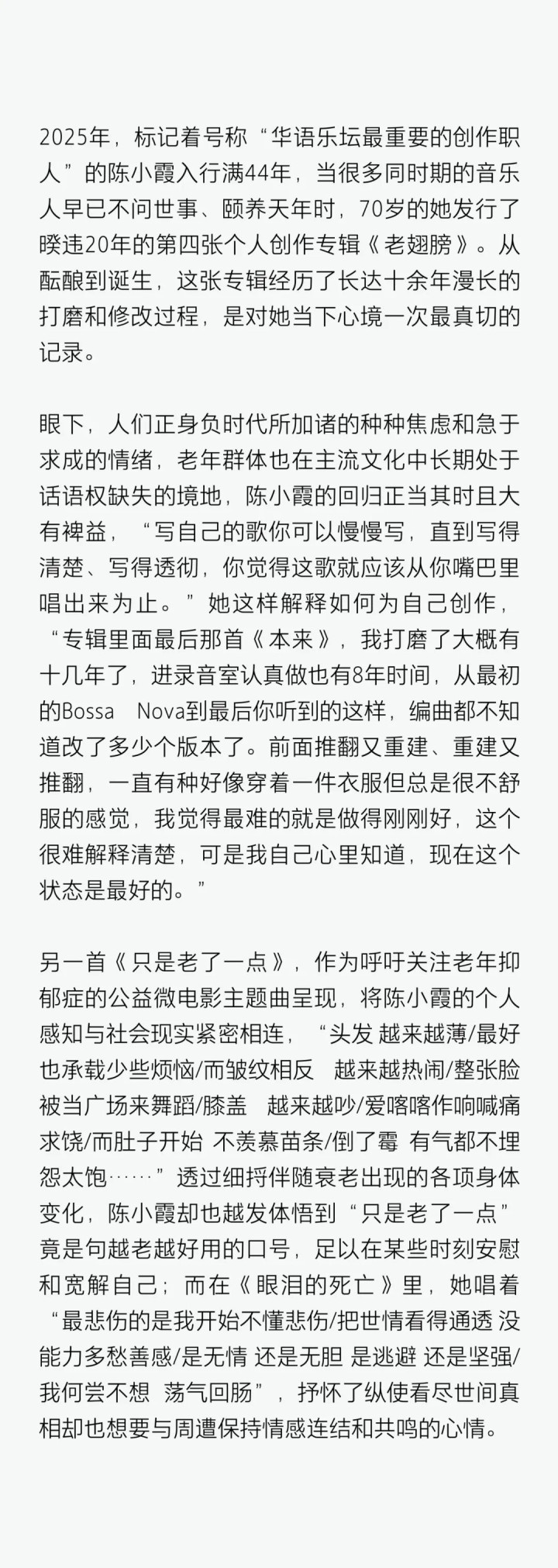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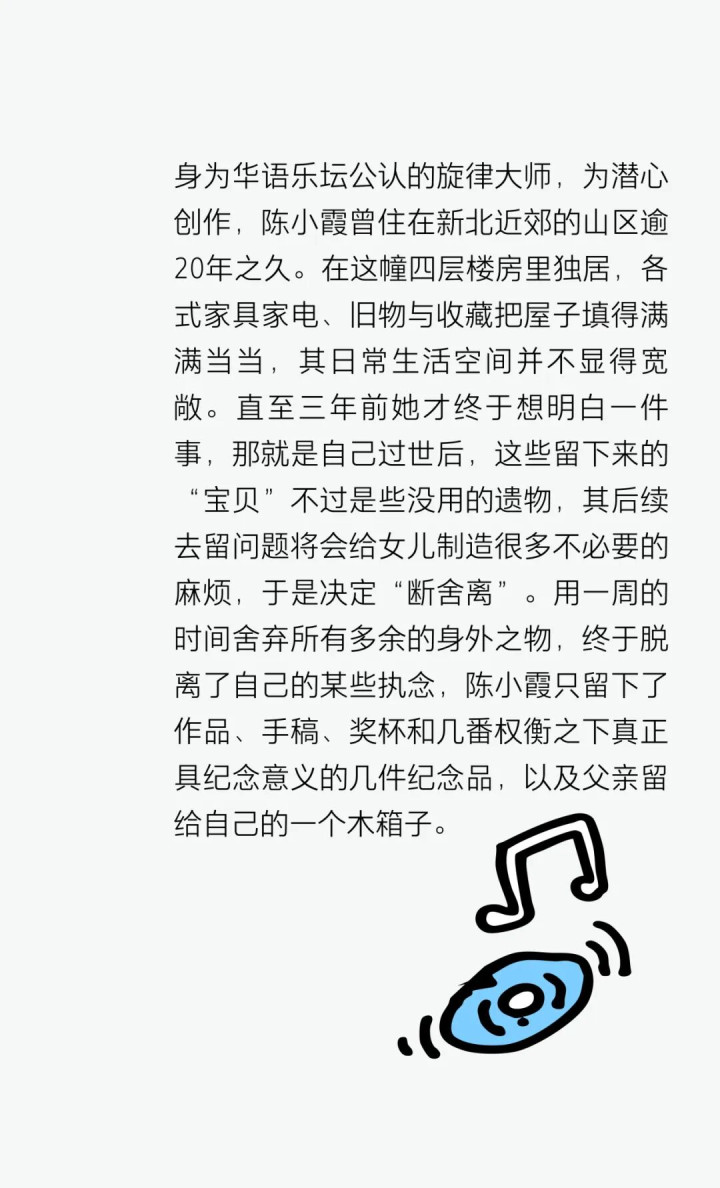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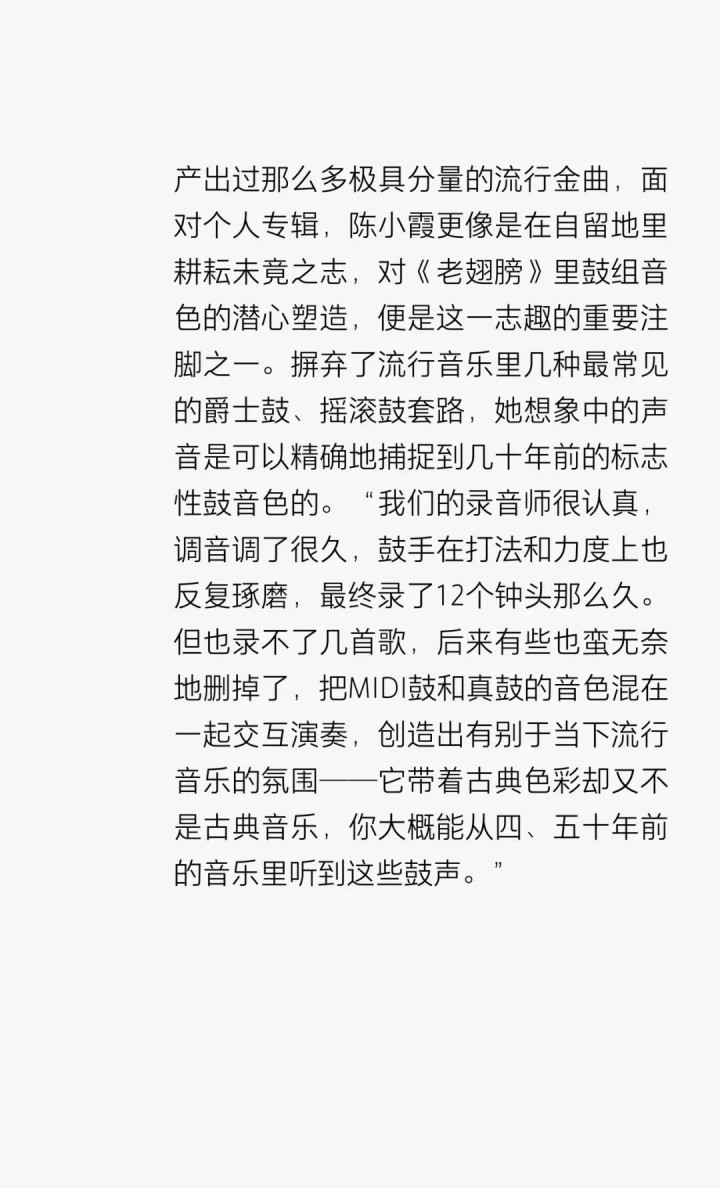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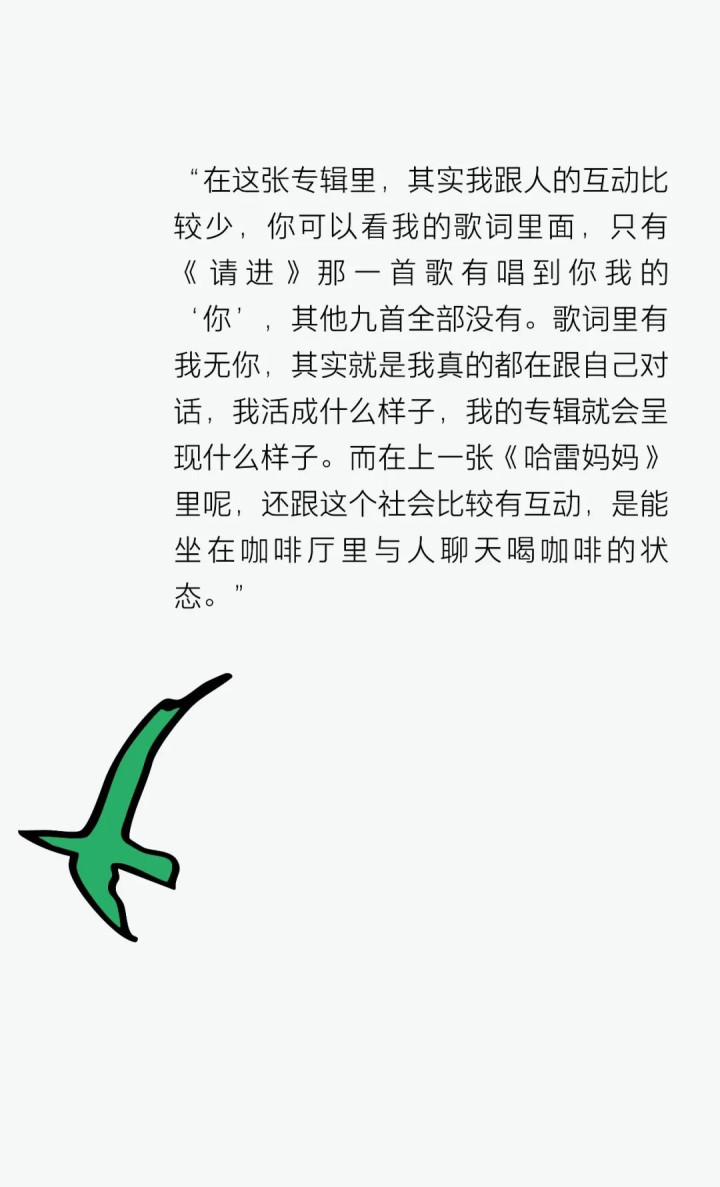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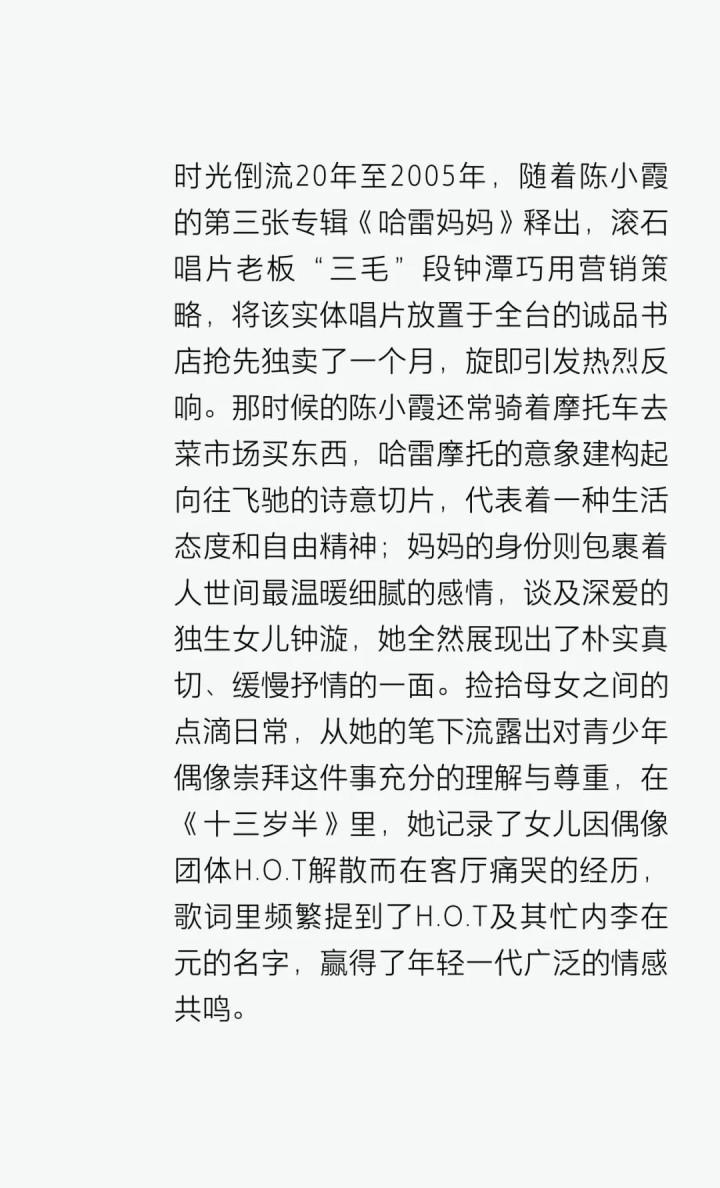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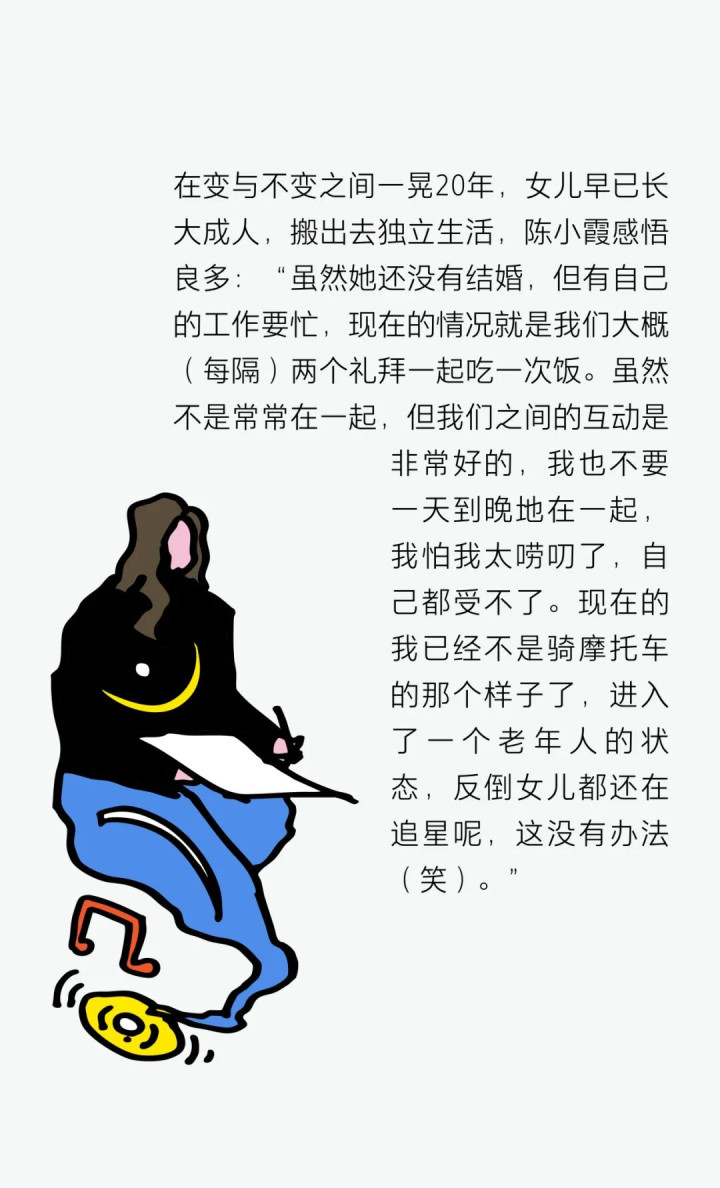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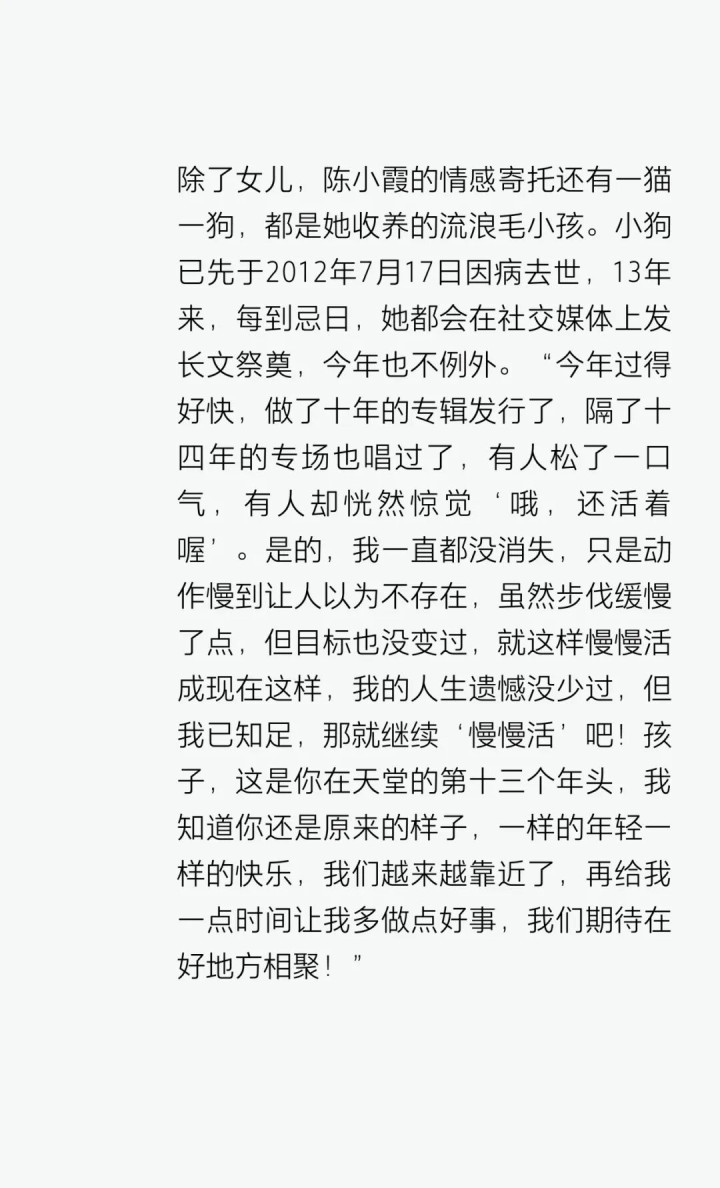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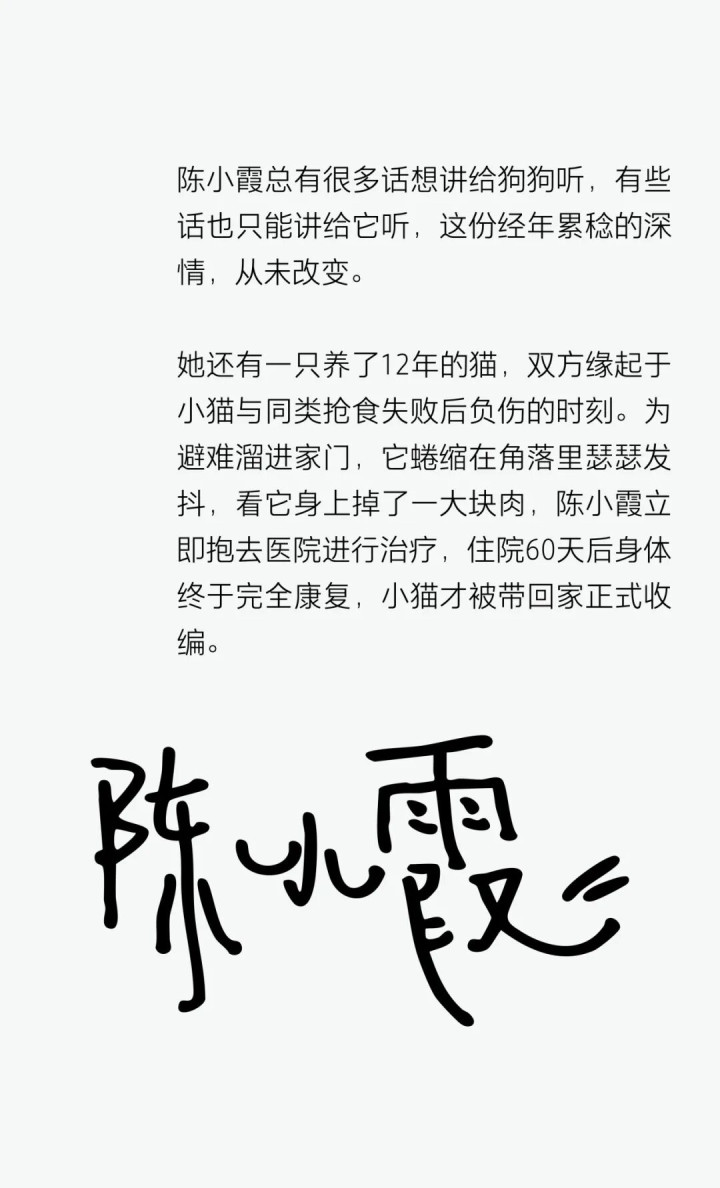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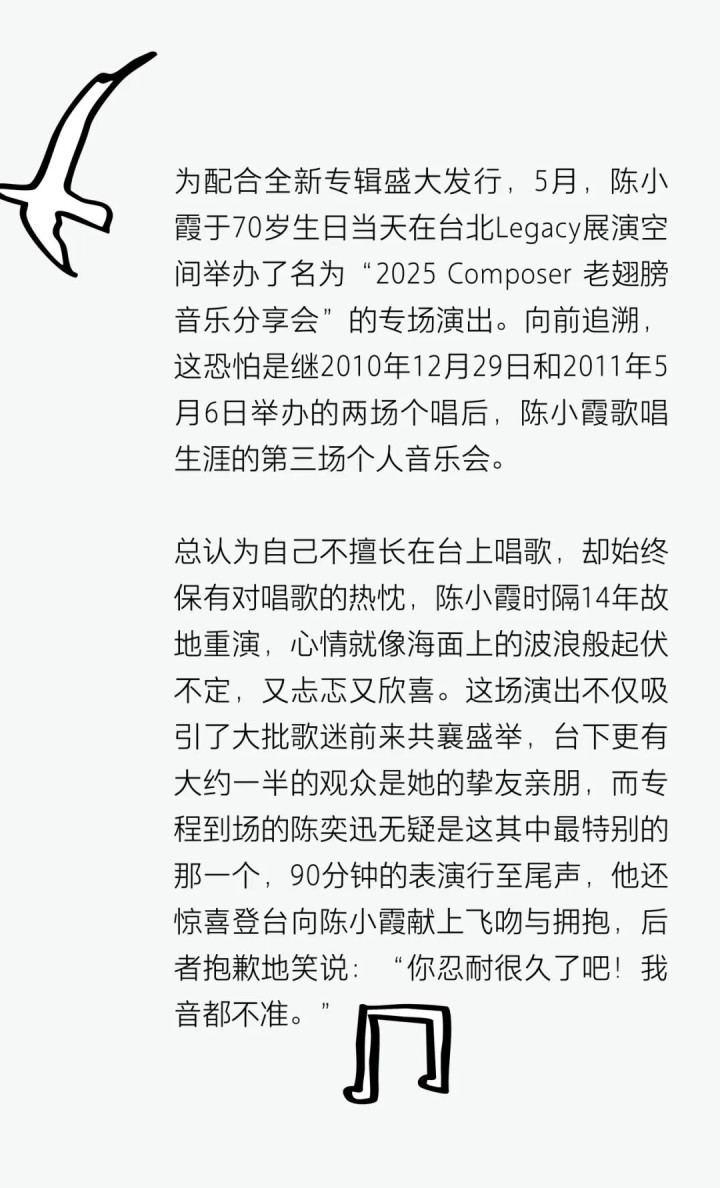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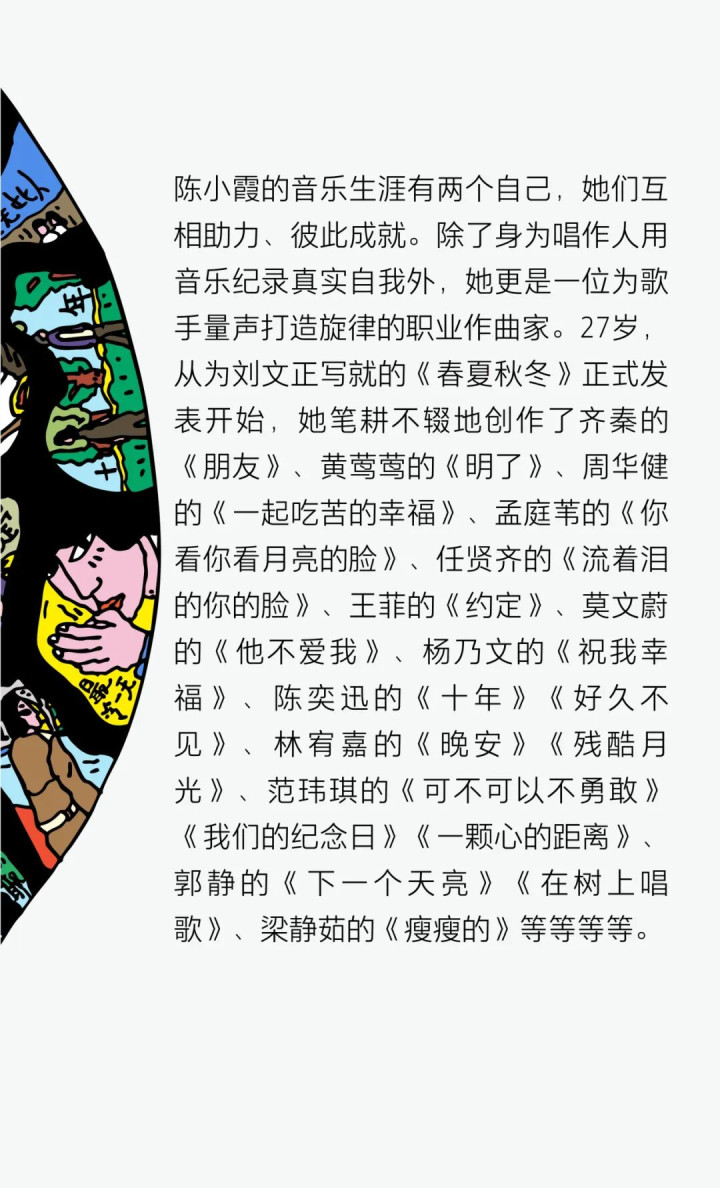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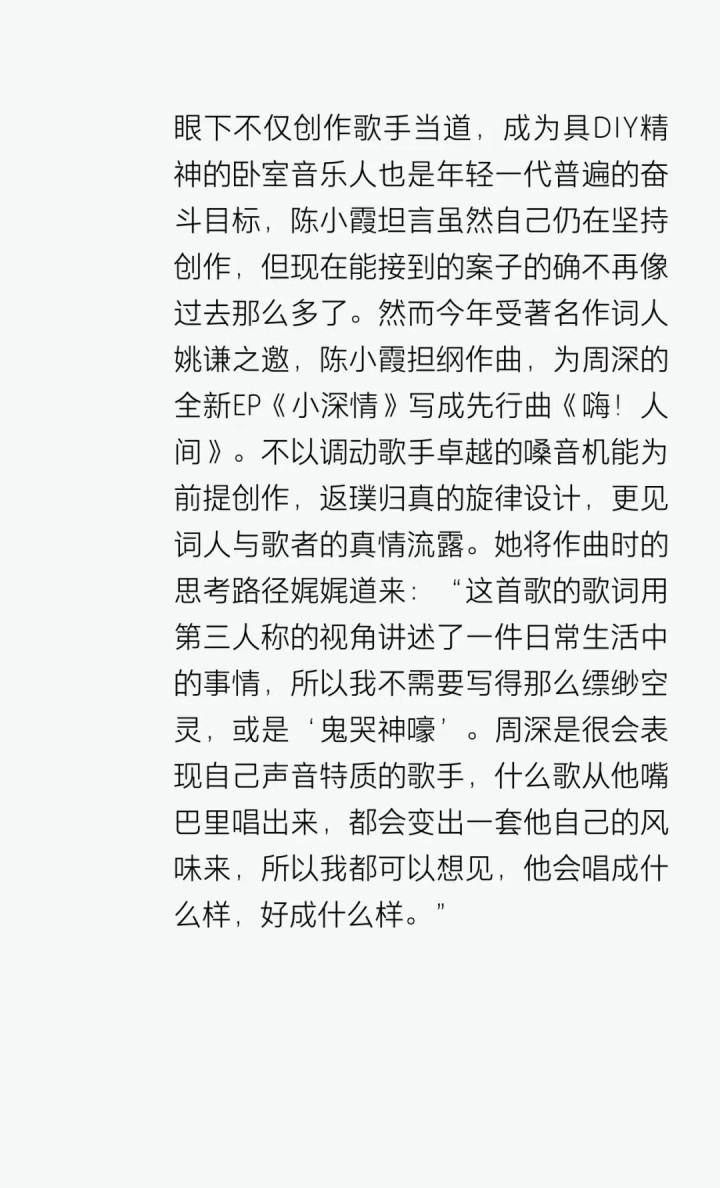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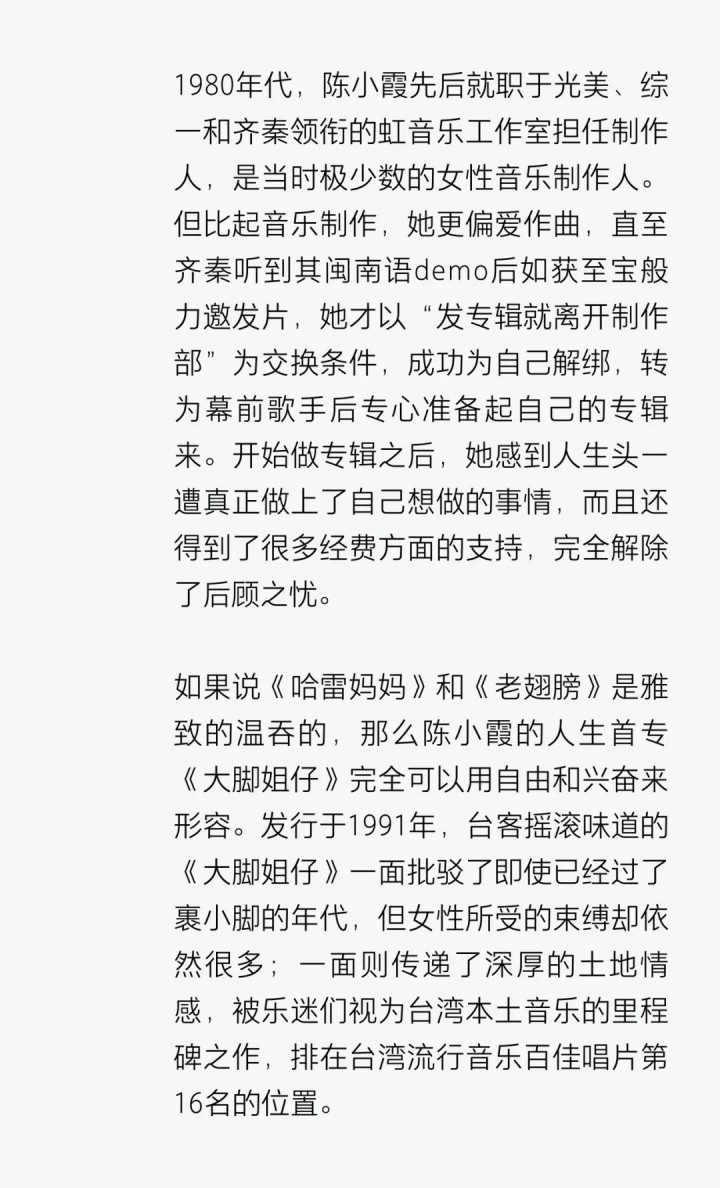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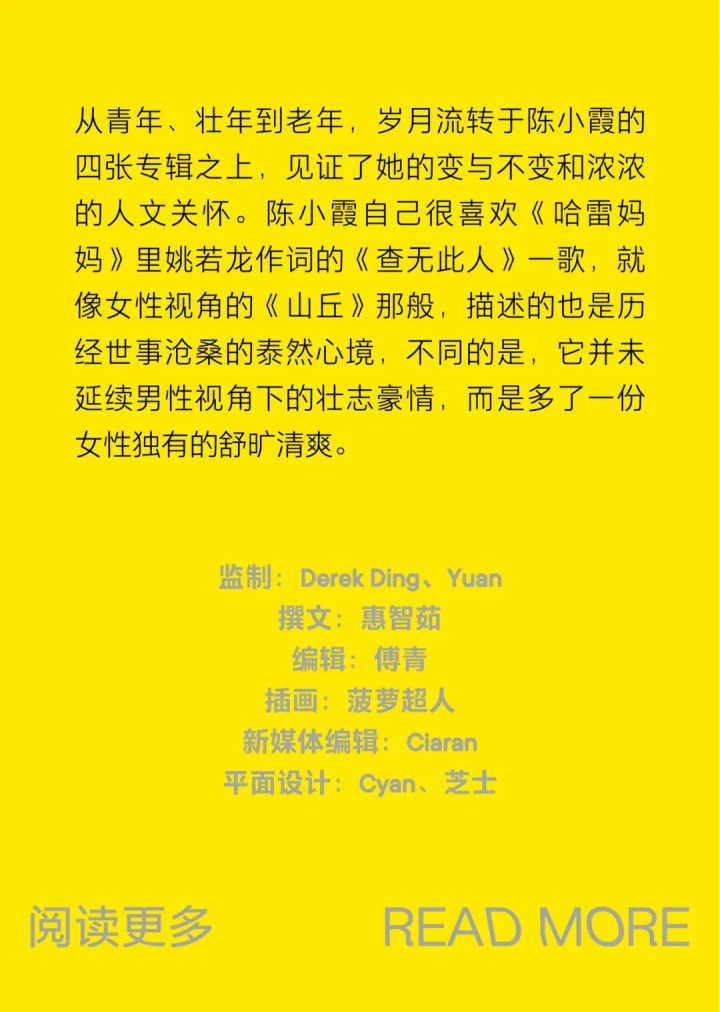
栏目:FACE面孔
西扎X马岩松:在混凝土里种树的人
The Architects Who Planted Time
撰稿:Casey
插画:菠萝超人
头图:
导语:91岁的西扎用布满褶皱的手捻起一张泛黄草图——他在等一棵树刺破混凝土,等一个东方追问者叩响时空之门。这里没有英雄宣言,只有两个建筑师在速朽的洪流里,打捞未被冲散的重量:关于一棵树的自由,关于慢的锋芒,关于如何用一生把建筑熬成呼吸。
正文:
在波尔图一个堆满了半个世纪尘埃与灵感的房间里,91岁的阿尔瓦罗.西扎(以下简称西扎)用他缓慢而专注的目光,接住了来自东方的追问。马岩松,这位中国建筑界的“顶流”与叛逆者,跨越时空,前来叩问一位活着的传奇。
这是一场关于时间、诗意与专注的对话,发生在碎片化的时代,却试图打捞起建筑最本真的重量。2024年5月马岩松受朱丽康(一言一吾i-Talk)邀请,拍摄《我与建筑师有个约会》,前往葡萄牙波尔图拜访91岁的普利兹克奖得主西扎,双方就建筑的本质、个人创作哲学进行了深度对话。短片入围第17届首尔国际建筑电影节,并于9月13日在首尔做韩国首映,以及第25届鹿特丹建筑电影节,于10月9日在荷兰鹿特丹做欧洲首映。
《NYLON尼龙》跟随纪录片的镜头与叙述,试图还原这场跨越九十载的相遇,并在两位建筑师身上,窥见一种未被洪流冲散的信念——关于如何与建筑相处一生。
小标:画笔、烟斗与一棵树
工作室的门被推开,光线涌入,照亮空气中悬浮的微尘。2024年5月,葡萄牙波尔图,马岩松终于走进了阿尔瓦罗·西扎的世界。这里不像一个办公室,更像一个时间的窖藏室。高耸的档案架上,塞满了泛黄的草图卷宗;桌边、墙角,散落着跨越数十年的建筑模型,像一座微缩城市的废墟与新生。91岁的西扎就坐在其中,像一座沉静的灯塔。
对谈开始了,但气氛更像一场老友的午后闲谈。尽管,这是一场险些未能发生的会面。制片人朱丽康在镜头外捏了一把汗。拍摄前两周,西扎先生刚因年迈的身体状况住进了医院。“我们当时心都凉了,心想这下完了。”朱丽康回忆道。但一个礼拜后,事务所传来消息:西扎来上班了。画图是西扎的精神疗愈,只要身体允许,他每天准时到工作室开始画图,雷打不动。
图注:影片《建筑中诗意与哲思》花絮39©一言一吾i-Talk
采访中,西扎偶尔会累,需要休息,但他的手从未真正停下。即使在聆听马岩松说话时,他的铅笔也会在纸上无意识地游走,勾勒出人物的侧脸线稿、一缕烟的形状、或是窗外树梢的弧度。“这应该是一种肌肉记忆,”朱丽康觉得这近乎一种虔诚的本能,“我们拿书请他签名,他看着自己书里的图,甚至会喃喃自语‘这画得有点眼熟,这是我画的吗?’他的时间阈值是5年、10年起的,30年前画的草图,在他口中如同昨日。”
而对马岩松来说,这次见面圆了一个夙愿。“我其实挺忙的,老是出差,按理说也没时间去拍什么片,”他语速很快,接受采访时正在导时差,但听起来心情不错,甚至透着一种幽默感,“西扎是我早就想见的。”他坦言,自己办公室的团队曾专门去葡萄牙朝圣西扎的建筑,但那次没见着人,一直是个遗憾。
马岩松对见这些老建筑师颇有兴趣,“像库哈斯、埃森曼,还有西扎,都是我年轻时上学就觉得了不起的人物。那时候也不知道怎么跟他们对话,现在觉得能见面聊一聊,真挺好的。”
提及对西扎的第一印象,马岩松脱口而出,“他总是慢悠悠的。可能是年龄,也可能是葡萄牙的节奏。他不怎么说很多话,除非你问他,更不会抢话,节奏一点也不快。”他特别注意到西扎如何看东西,“他看图纸、看照片、看书,会盯着琢磨半天。哪怕是自己以前作品的图,也看得特别仔细。好像过了一段时间,他又能从中发现新的东西。”这种慢,在马岩松看来,是一种强大的能力。“节奏慢才能观察和感受到更多东西,太快了,肯定会忽略很多。”
西扎的手,是一双会讲故事的手,布满了皱纹,却稳如磐石。镜头紧紧跟随着这双手,它抚摸过上世纪模型的肌理,它握紧铅笔,在空白纸上赋予线条生命。“他挺神的,我觉得他是能当艺术家的那种建筑师,”马岩松不吝赞美,“不是一般画建筑,他能画人、画动物、画风景。”他观察到,西扎的画并非写实性的复刻,而是捕捉瞬间的艺术。“他关注一些有生活感的瞬间,抓住现实中的片段。这肯定跟观察有关,他关心的是你的动作、小细节、姿态,或是自然中他觉得美的线条。”
这种观察力,渗透在西扎建筑的每一个毛孔里。马岩松将其总结为——一个美丽的房间,有一个美丽的窗户。“我们一般对一个房间很少有感觉,考虑的都是尺寸、功能、怎么摆家具。但他的房间,形状、比例就让人感觉舒服。然后在恰到好处的地方开一扇窗,大小、比例极漂亮,引入室外的光线和景色,那里可能正好有棵树。”
马岩松感慨:”就这么一个简单的房间,对任何普通人来说,对建筑空间的感受就应该这样吧?但这很难,我发现很少有建筑师能做到。而西扎的很多房间,美术馆、办公室、教堂,每一个都这么漂亮。这是一种艺术修养,出手比例就好,差一点就不舒服。这不是黄金分割公式能解决的,这是一种感受力。”
这也引向了对话中最锋利也最诗意的一刻,马岩松抛出了那个酝酿已久的问题:“您的建筑里,总有一棵树被围在墙里,它是否失去了自由?”这是一个东方灵魂对西方大师关于禁锢与生长的哲学叩问。西扎沉思了良久,之后缓缓开口:“也许我走了,就看不到它生长了。但我的儿子、我的孙子会见证。它其实是一代一代的传承。”
一句话,将建筑的维度从空间拉向了时间。朱丽康对此印象深刻:“建筑需要留下来给后人一些东西,慢慢成长,有一种代际传承的概念。”她想象着,“假如有个小朋友一直在建筑里玩,他长大了,去读大学、工作,再回来时那棵树还在。这个地点就有了独特的精神属性,承载着他所有的回忆。”
马岩松的理解则更贴近本质:“这棵树在他的记忆里是什么样子?他小时候看到什么树?树的成长,赋予了一个地点、一段记忆。树在进入建筑之前,其实已经成为作品的一部分。”这些话,连接着记忆与感觉,非常感性,也彻底印证了马岩松的猜想——西扎是一个极其感性的人。
小标:珍贵的感性
“您觉得自己是感性还是理性的?”当马岩松被问及这个问题,他轻笑一声,答案非常明确:“我肯定偏感性,我甚至比西扎还感性一点。但我也不是像弗兰克·盖里那种‘很疯’的感性。”
在马岩松看来,西扎的独特在于其双重性。“你可以从两方面理解他。传统的建筑师会认为他是现代主义的,空间、材料、构成,很理性、思维缜密、追求完美。但我觉得他骨子里是感性的,他许多空间的处理非常浪漫、诗意,也不追求绝对的精确,有很多留白。”
与西扎的对谈,更加强化了马岩松的印象。“他挺符合我对他的期待的,他是主观的、感性的。大部分建筑师不这样说话,他们跟工程技术打交道更多,没那么感性。”马岩松甚至觉得,西扎更像一个小说家、导演或作家,“因为他关心那些东西,他的表达很感性。”这种感性,让马岩松产生了强烈的共鸣。
“一个简单的房间,比例、尺寸、开窗的位置、光线的落点,一切都恰到好处。差一点,就不对劲了。”西扎的这种能力,不是靠公式或黄金分割,而是靠一种近乎艺术家的感受力。“他不是在计算美,他是在感受美。”马岩松如是说。
“西扎来自葡萄牙,在欧洲也算边缘,不是文化霸权中心。但他的建筑建立了自己独特的语言,不那么贵,不依赖高技术或经济实力,却有一种回应了现代性的诗意,一种个人和地方的诗意。”马岩松话锋一转,提到了中国,“我们其实也面对类似情况。中国经济和技术不差了,但能用建筑建造出中国人诗意栖居的,非常少。我们缺少那种放松又自信的状态。大部分情况是,要么一味学西方,要么一味反对西方,这两种心态都不正常,从根本上来讲,都是以西方为标准。没有西扎那种很自然的心态,没有一个自己的现代性表达。”
马岩松不讳言自己的处境:“我自己确实就在这种处境下,总想去争取一个位置,在西方主导的话语权里希望有自己的位置。”因此,西扎的成功对他而言是一种鼓舞和印证——“他绝对是做到了,不是靠地域风情或政治正确,他的作品放在欧美日本任何重要的文化设施里,都完全可以。”
在西扎的工作室里,马岩松看到了这个时代最稀缺的资源:专注。那里没有智能手机的频繁闪烁,没有社交媒体的信息洪流,只有一台像是装饰品的90年代老电视机。西扎活在时间的褶皱里,用最原始的工具——铅笔与纸,与世界对话。“西扎看东西从不轻撇一眼,而是停下来思考。这种专注是建筑师进入自我世界的钥匙。”马岩松对此深感震撼。在一个被15秒短视频统治注意力的时代,这种深度沉浸,几近一种抵抗。
图注:影片《建筑中诗意与哲思》花絮39©一言一吾i-Talk
这份专注保护了西扎,让他免受外界杂音的干扰,更完整地守护了自己的建筑世界。马岩松甚至由此联想到当下激烈的网络环境:“像高迪、西扎这样的人,如果暴露在今天的环境里,会怎样?葡萄牙给了西扎一个舒服、放松的文化和自然环境。”
在朱丽康看来,马岩松同样拥有这种专注力。“他那么忙,去年还出了一本10万字的书,说是疫情封控在酒店没事干写的。当他沉浸在工作里,效率会非常高。”
专注不仅是一种工作方法,更是一种精神抵抗。在西扎身上,马岩松看到了一种未被现实溶解的完整性。“他不在乎外界怎么说,他就是画他的图,做他的房子。所以他才能创造出一个个完整的世界。”完整性,恰恰是马岩松认为当代建筑最缺乏的东西:“妥协太多,作品就不完整了。你看高迪,他建造的世界那么超现实,根本不属于他所在的时代,正因为他不妥协,才能跨越百年依然打动人心。”
小标:把建筑当生活
通过几次纪录片的拍摄,朱丽康看到了一个立体、变化着的马岩松。“大众眼里的马岩松是野心写在脸上的狂人,标签很多,顶流、很酷、很狂、直言不讳。”但随着接触的深入,让她看到了马岩松锋刃下的柔光。
大众眼中的马岩松,是那个说出“我不在乎别人喜不喜欢”的狂人,是那个设计出梦露大厦、哈尔滨大剧院的先锋者。但朱丽康在三次纪录片合作中,看到了他另一面——“他从前一种带着征服世界的劲头儿,但现在越来越温柔了。”
这种温柔,体现在他近年的公共项目中——嘉兴火车站用自然光包裹旅人,衢州体育场用曲线软化庞大体量。“他开始考虑普通人是否被尊重、是否舒服,建筑是否能包裹人的脆弱。他的作品,外观是曲线的、张扬的,但底色是温暖的。他有先锋建筑师的锋芒与突破精神,也有作为建筑师的社会责任感,对普通人和生活的关怀,他是刚柔并济的。”
聊到工作状态,马岩松的拼有了更为具象的画面。朱丽康见识过马岩松硬扛的功力。“他全球飞,没有时差,精力无限。拍摄时他可能前一天刚从美国飞过来,马上投入工作,一直表达一直说。我问他,你怎么保持这种精力?他就说俩字,硬扛!他也累,但就是能扛下来。”
这种“硬扛”,源于一种强大的内驱力与先锋者的自觉。马岩松曾以山水城市的乌托邦构想挑战行业,也曾在争议中坚持己见。他说自己“已经算不太妥协的人了”,甚至常被人认为过于自我,但面对优秀建筑师的作品,依然会不断反思,“看到这些伟大建筑师的作品,总会觉得自己有妥协。妥协多了,作品就不完整了。但只有完整的世界观才能跨越时间,才能打动人心。”
在西扎身上,马岩松看到了一种终极化解之道——把建筑变成生活,而非职业。
图注:影片《建筑中诗意与哲思》花絮39©一言一吾i-Talk
“我觉得如果他这个工作得成为一种享受,不能成为一个负担。”马岩松描绘了一幅令人神往的图景,“他画一个草图,就跟喝一杯咖啡一样舒服。今天想喝,昨天喝了,明天还要喝。到90岁他还想喝。这很自然。”
反之,“如果你觉得这是工作,那就很费劲了,这是一项要完成任务,我本来想去喝咖啡的,非得让我画图,那就完了。最好早点结束,千万别等到老了还这么想。”
这也是马岩松最想对年轻建筑师说的一句话:“把建筑当生活。生活是自己的,表达也是自己的。如果你老想着市场、饭碗、别人喜不喜欢,那就很难走下去。”西扎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证明:建筑不是一条必须越走越窄的职业赛道,而是一种可以持续一生的生活方式。“你做到90岁,也不会有人让你退休,重要的是,你还能和它融洽相处。”
西扎依旧每天11点准时出现在工作室,画图、抽烟、看树。他那些被围墙禁锢的树,终将穿透混凝土的边界,长成时间的一部分。在这场跨越九十载的对话中,没有英雄主义的宣言,没有技术至上的狂欢,只有两个建筑师在诗意的废墟上,寻找某种未灭的火焰。
一如马岩松所说:“建筑最终是要留给时间的。”
2003年前后,当陈奕迅在香港之外还只是个眼熟却叫不出名字的歌手时,路人会称呼他为“唱《十年》的那个人”。如今,这位陈奕迅口中”用旋律讲故事的人”,在70岁这一年,带着专辑《老翅膀》温柔归来,用新作诠释岁月沉淀后的放下与自由。她就是陈小霞。 2025年,标记着号称“华语乐坛最重要的创作职人”的陈小霞入行满44年,当很多同时期的音乐人早已不问世事、颐养天年时,70岁的她发行了暌违20年的第四张个人创作专辑《老翅膀》。从酝酿到诞生,这张专辑经历了长达十余年漫长的打磨和修改过程,是对她当下心境一次最真切的记录。 眼下,人们正身负时代所加诸的种种焦虑和急于求成的情绪,老年群体也在主流文化中长期处于话语权缺失的境地,陈小霞的回归正当其时且大有裨益,“写自己的歌你可以慢慢写,直到写得清楚、写得透彻,你觉得这歌就应该从你嘴巴里唱出来为止。”她这样解释如何为自己创作,“专辑里面最后那首《本来》,我打磨了大概有十几年了,进录音室认真做也有8年时间,从最初的Bossa Nova到最后你听到的这样,编曲都不知道改了多少个版本了。前面推翻又重建、重建又推翻,一直有种好像穿着一件衣服但总是很不舒服的感觉,我觉得最难的就是做得刚刚好,这个很难解释清楚,可是我自己心里知道,现在这个状态是最好的。” 另一首《只是老了一点》,作为呼吁关注老年抑郁症的公益微电影主题曲呈现,将陈小霞的个人感知与社会现实紧密相连,“头发 越来越薄/最好也承载少些烦恼/而皱纹相反 越来越热闹/整张脸 被当广场来舞蹈/膝盖 越来越吵/爱喀喀作响喊痛求饶/而肚子开始 不羡慕苗条/倒了霉 有气都不埋怨太饱……”透过细捋伴随衰老出现的各项身体变化,陈小霞却也越发体悟到“只是老了一点”竟是句越老越好用的口号,足以在某些时刻安慰和宽解自己;而在《眼泪的死亡》里,她唱着“最悲伤的是我开始不懂悲伤/把世情看得通透 没能力多愁善感/是无情 还是无胆 是逃避 还是坚强/我何尝不想 荡气回肠”,抒怀了纵使看尽世间真相却也想要与周遭保持情感连结和共鸣的心情。 音符化作翅膀,生命飞得更高 身为华语乐坛公认的旋律大师,为潜心创作,陈小霞曾住在新北近郊的山区逾20年之久。在这幢四层楼房里独居,各式家具家电、旧物与收藏把屋子填得满满当当,其日常生活空间并不显得宽敞。直至三年前她才终于想明白一件事,那就是自己过世后,这些留下来的“宝贝”不过是些没用的遗物,其后续去留问题将会给女儿制造很多不必要的麻烦,于是决定“断舍离”。用一周的时间舍弃所有多余的身外之物,终于脱离了自己的某些执念,陈小霞只留下了作品、手稿、奖杯和几番权衡之下真正具纪念意义的几件纪念品,以及父亲留给自己的一个木箱子。 其后,改变住家环境只身搬到台北,有如身处一片净土乌托邦之地,陈小霞感到久违的轻盈,随之自觉有一股力量正沿脊柱上行,那是一双收在背后很久欲振翅飞翔的翅膀。她从中得到启发,写下专辑同名曲《老翅膀》,讲述了“放下”与“飞翔”的故事:无论到了什么年纪,人都拥有“翅膀”,哪怕已是一双“老翅膀”了,也蕴藏着生命中未被发觉的力量,只要肯放下过去的负累,就能飞向更广阔的自由天地。 自前作《哈雷妈妈》起,陈小霞的个人作品便沾染上了些许古雅的温柔民谣风味,而这张《老翅膀》贯通古典乐气韵,更从优雅沧桑的歌声里透出创作者古稀之年的睿智光芒,她却用“温吞”一词来形容如此基调,“‘温吞’代表这样的作品丢到市场上不可能让你眼前一亮,也代表筹备专辑的那几年我大概就是这个状态。”陈小霞进一步解释说。援引巴赫名曲《G弦上的咏叹调》,融汇小号、原声吉他与大提琴,亦有强烈的陈辉阳式弦乐编排贯穿期间,《还活着》可谓全专在声响上的极致代表,在抚慰人心的旋律里,举重若轻地倾诉着“很幸运能有权力唱出悲观的自己”。 产出过那么多极具分量的流行金曲,面对个人专辑,陈小霞更像是在自留地里耕耘未竟之志,对《老翅膀》里鼓组音色的潜心塑造,便是这一志趣的重要注脚之一。摒弃了流行音乐里几种最常见的爵士鼓、摇滚鼓套路,她想象中的声音是可以精确地捕捉到几十年前的标志性鼓音色的。“我们的录音师很认真,调音调了很久,鼓手在打法和力度上也反复琢磨,最终录了12个钟头那么久。但也录不了几首歌,后来有些也蛮无奈地删掉了,把MIDI鼓和真鼓的音色混在一起交互演奏,创造出有别于当下流行音乐的氛围——它带着古典色彩却又不是古典音乐,你大概能从四、五十年前的音乐里听到这些鼓声。” “在这张专辑里,其实我跟人的互动比较少,你可以看我的歌词里面,只有《请进》那一首歌有唱到你我的‘你’,其他九首全部没有。歌词里有我无你,其实就是我真的都在跟自己对话,我活成什么样子,我的专辑就会呈现什么样子。而在上一张《哈雷妈妈》里呢,还跟这个社会比较有互动,是能坐在咖啡厅里与人聊天喝咖啡的状态。” 时光倒流20年至2005年,随着陈小霞的第三张专辑《哈雷妈妈》释出,滚石唱片老板“三毛”段钟潭巧用营销策略,将该实体唱片放置于全台的诚品书店抢先独卖了一个月,旋即引发热烈反响。那时候的陈小霞还常骑着摩托车去菜市场买东西,哈雷摩托的意象建构起向往飞驰的诗意切片,代表着一种生活态度和自由精神;妈妈的身份则包裹着人世间最温暖细腻的感情,谈及深爱的独生女儿钟漩,她全然展现出了朴实真切、缓慢抒情的一面。捡拾母女之间的点滴日常,从她的笔下流露出对青少年偶像崇拜这件事充分的理解与尊重,在《十三岁半》里,她记录了女儿因偶像团体H.O.T解散而在客厅痛哭的经历,歌词里频繁提到了H.O.T及其忙内李在元的名字,赢得了年轻一代广泛的情感共鸣。 在变与不变之间一晃20年,女儿早已长大成人,搬出去独立生活,陈小霞感悟良多:“虽然她还没有结婚,但有自己的工作要忙,现在的情况就是我们大概(每隔)两个礼拜一起吃一次饭。虽然不是常常在一起,但我们之间的互动是非常好的,我也不要一天到晚地在一起,我怕我太唠叨了,自己都受不了。现在的我已经不是骑摩托车的那个样子了,进入了一个老年人的状态,反倒女儿都还在追星呢,这没有办法(笑)。” 除了女儿,陈小霞的情感寄托还有一猫一狗,都是她收养的流浪毛小孩。小狗已先于2012年7月17日因病去世,13年来,每到忌日,她都会在社交媒体上发长文祭奠,今年也不例外。“今年过得好快,做了十年的专辑发行了,隔了十四年的专场也唱过了,有人松了一口气,有人却恍然惊觉‘哦,还活着喔’。是的,我一直都没消失,只是动作慢到让人以为不存在,虽然步伐缓慢了点,但目标也没变过,就这样慢慢活成现在这样,我的人生遗憾没少过,但我已知足,那就继续‘慢慢活’吧!孩子,这是你在天堂的第十三个年头,我知道你还是原来的样子,一样的年轻一样的快乐,我们越来越靠近了,再给我一点时间让我多做点好事,我们期待在好地方相聚!” 陈小霞总有很多话想讲给狗狗听,有些话也只能讲给它听,这份经年累稔的深情,从未改变。 她还有一只养了12年的猫,双方缘起于小猫与同类抢食失败后负伤的时刻。为避难溜进家门,它蜷缩在角落里瑟瑟发抖,看它身上掉了一大块肉,陈小霞立即抱去医院进行治疗,住院60天后身体终于完全康复,小猫才被带回家正式收编。 “陈小霞式旋律” 为配合全新专辑盛大发行,5月,陈小霞于70岁生日当天在台北Legacy展演空间举办了名为“2025 Composer 老翅膀音乐分享会”的专场演出。向前追溯,这恐怕是继2010年12月29日和2011年5月6日举办的两场个唱后,陈小霞歌唱生涯的第三场个人音乐会。 总认为自己不擅长在台上唱歌,却始终保有对唱歌的热忱,陈小霞时隔14年故地重演,心情就像海面上的波浪般起伏不定,又忐忑又欣喜。这场演出不仅吸引了大批歌迷前来共襄盛举,台下更有大约一半的观众是她的挚友亲朋,而专程到场的陈奕迅无疑是这其中最特别的那一个,90分钟的表演行至尾声,他还惊喜登台向陈小霞献上飞吻与拥抱,后者抱歉地笑说:“你忍耐很久了吧!我音都不准。” “我为什么看到Eason会跟他讲‘抱歉’‘辛苦’呢,因为他的耳朵非常好,我边唱就在想,‘完了,这句走音’‘完了,他一定在皱眉头’,尤其从我这个视角看过去,根本找不到他(笑)。跟14年前的那场比起来,有些东西没变,有些东西变了,我真觉得我没唱好,明显感到体能变差了,但有的东西又变得更好了,这就是整个过程有趣的地方,如果我跟14年前一模一样地站在这里,想必大家也会很失望的。” 不止这次在场,有几个老歌迷也曾深情奔赴前两个十几年前的专场,他们的全勤参与令陈小霞不禁感动。听闻当晚签名会结束后,四名歌迷一直聚在Legacy门外聊天,直至临近午夜场地把门口的桌子都收走了仍迟迟不肯离去,陈小霞表示若当时了解如此情况,一定会上前当面打个招呼。“我觉得他们好乖,有那种要送礼物的呢,就托人送给我,他就躲在角落边边比一下那个东西是他送的,然后就走了。我也没有很多粉丝,我想应该是这样,他们大概在生活中很难碰到可以一起聊我的音乐的朋友,所以来这边碰在一起就大聊特聊起来,我懂那种心情。”静静地互相陪伴,粉丝是来看偶像的,偶像又何尝不是来看粉丝的呢。 2006年携《哈雷妈妈》来北京做宣传,陈小霞曾在记者会上抱着小吉他自弹自唱地演唱了两首歌,此外,她至今未在大陆真正登台表演过。而这一次,官宣个人专场即将首次落地广州和北京的消息,对于广大陈小霞的大陆歌迷而言,无疑是翘首以盼的巨大惊喜。2025年10月31日和2025年11月2日,分别在广州中央车站展演中心和北京蛙厂RMMF·798店,大陆的观众将有幸近距离感受“2025 Composer 老翅膀音乐分享会”的非凡魅力。陈小霞逗趣地说:“我跟你讲,我是‘稀世珍宝’(笑)。” 陈小霞的音乐生涯有两个自己,她们互相助力、彼此成就。除了身为唱作人用音乐纪录真实自我外,她更是一位为歌手量声打造旋律的职业作曲家。27岁,从为刘文正写就的《春夏秋冬》正式发表开始,她笔耕不辍地创作了齐秦的《朋友》、黄莺莺的《明了》、周华健的《一起吃苦的幸福》、孟庭苇的《你看你看月亮的脸》、任贤齐的《流着泪的你的脸》、王菲的《约定》、莫文蔚的《他不爱我》、杨乃文的《祝我幸福》、陈奕迅的《十年》《好久不见》、林宥嘉的《晚安》《残酷月光》、范玮琪的《可不可以不勇敢》《我们的纪念日》《一颗心的距离》、郭静的《下一个天亮》《在树上唱歌》、梁静茹的《瘦瘦的》等等等等。 再以前文的陈奕迅为例,两人的初次合作始于2001年发行的《Shall We Dance? Shall We Talk!》里的《黑暗中漫舞》,转年又二搭《明年今日》,即《十年》的粤语原版。直至收录《十年》的国语概念专辑《黑.白.灰》问世,“十年之前/我不认识你 你不属于我/ 我们还是一样/陪在一个陌生人左右/走过渐渐熟悉的街头”的旋律开始席卷街头巷尾、电台与KTV,许多大陆和台湾歌迷才得以认识了这位港乐新一代“歌神”。2003年前后,当陈奕迅在香港之外还只是个眼熟却叫不出名字的歌手时,路人会称呼他为“唱《十年》的那个人”。 眼下不仅创作歌手当道,成为具DIY精神的卧室音乐人也是年轻一代普遍的奋斗目标,陈小霞坦言虽然自己仍在坚持创作,但现在能接到的案子的确不再像过去那么多了。然而今年受著名作词人姚谦之邀,陈小霞担纲作曲,为周深的全新EP《小深情》写成先行曲《嗨!人间》。不以调动歌手卓越的嗓音机能为前提创作,返璞归真的旋律设计,更见词人与歌者的真情流露。她将作曲时的思考路径娓娓道来:“这首歌的歌词用第三人称的视角讲述了一件日常生活中的事情,所以我不需要写得那么缥缈空灵,或是‘鬼哭神嚎’。周深是很会表现自己声音特质的歌手,什么歌从他嘴巴里唱出来,都会变出一套他自己的风味来,所以我都可以想见,他会唱成什么样,好成什么样。” 帮周深这么棒的歌手写歌,陈小霞感受得到其中的意义感,同时她也很珍视与姚谦共创的机会。“大概30年前,我有跟姚谦合写过一首给林慧萍的歌,具体什么歌名都有点忘了,还有一首是写给侯湘婷的《暧昧》,我们两个真的很少有机会合作。这次(能合作)很不容易,我也写得很认真,姚谦一直在找这首歌还可以再怎么样的可能性,我们来来回回调整了好几次才终于定稿。” 陈小霞的旋律里往往有一种极具辨识度的曲调回转,她将温情、治愈和淡淡哀愁共冶一炉,调配出独特的流行性和传唱度,人们亲切地称之为“陈小霞式旋律”。这种被同行和听众辨识的个人印记,陈小霞并不自知:“说实话我真的不知道,有时候我无法理解为什么人家那么厉害,一听就知道是我的东西。可能我的歌里面透露出一些我惯用的转折,或者是几个常常会用的音符。也可能是作品多,大家听惯了?有人写歌都会说‘诶,我这是学陈小霞写的。’我一听还真有那个味道。真的不知道要怎么说,可能我的审美观、美感度就是这样吧。” “我的闽南语歌” 1980年代,陈小霞先后就职于光美、综一和齐秦领衔的虹音乐工作室担任制作人,是当时极少数的女性音乐制作人。但比起音乐制作,她更偏爱作曲,直至齐秦听到其闽南语demo后如获至宝般力邀发片,她才以“发专辑就离开制作部”为交换条件,成功为自己解绑,转为幕前歌手后专心准备起自己的专辑来。开始做专辑之后,她感到人生头一遭真正做上了自己想做的事情,而且还得到了很多经费方面的支持,完全解除了后顾之忧。 如果说《哈雷妈妈》和《老翅膀》是雅致的温吞的,那么陈小霞的人生首专《大脚姐仔》完全可以用自由和兴奋来形容。发行于1991年,台客摇滚味道的《大脚姐仔》一面批驳了即使已经过了裹小脚的年代,但女性所受的束缚却依然很多;一面则传递了深厚的土地情感,被乐迷们视为台湾本土音乐的里程碑之作,排在台湾流行音乐百佳唱片第16名的位置。 拥有最大程度的创作自由,陈小霞恣意融入了多种音乐元素,在开篇曲《傀儡尪仔》里加入了具画龙点睛之效的唢呐,“台湾二胡之王”温金龙为《你和我的电影》激情献奏,仔细听《鱼》这首歌,还贯入了巴乌舒缓且闷闷的声音…… 在专辑内页里,陈小霞还以《我的闽南语歌》为题,写下一段动人文字:我那本省籍妈妈认识我那外省籍爸爸时,国语只会说“就是我了啦!”婚后,妈妈的国语还是没啥进步,原因是爸爸用国语说话时,妈妈还是以闽南语回答。做孩子的我们,在一家六口的饭桌上,和爸爸说话用国语,和妈妈说话便用闽南语。这情形,在我这代和新一代间很普遍。于是产生了一种新的国语和闽南语,这是文化联姻的结果。但这不重要,就像我妈妈和我爸爸的结合,他们依侍的是情感,我的闽南语歌也是。 和《大脚姐仔》两相对照,陈小霞速度空前地于两年后再推二专《化妆师》,与首张专辑描绘外在表象不同,这张专辑转向内心世界的剖析,“我还讲说最好的化妆就是洗脸(笑)。” 从青年、壮年到老年,岁月流转于陈小霞的四张专辑之上,见证了她的变与不变和浓浓的人文关怀。陈小霞自己很喜欢《哈雷妈妈》里姚若龙作词的《查无此人》一歌,就像女性视角的《山丘》那般,描述的也是历经世事沧桑的泰然心境,不同的是,它并未延续男性视角下的壮志豪情,而是多了一份女性独有的舒旷清爽。
